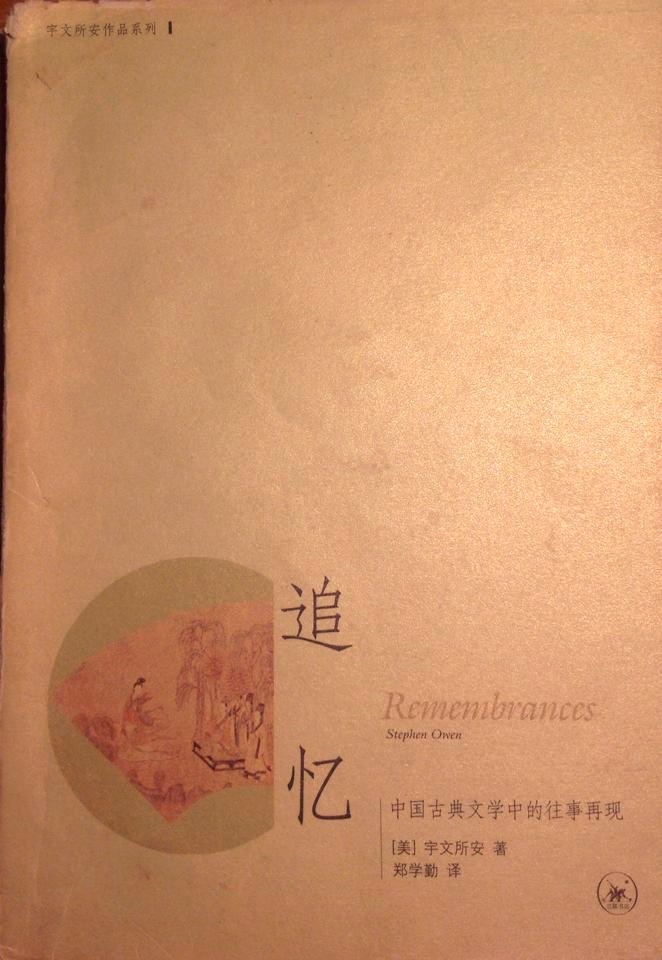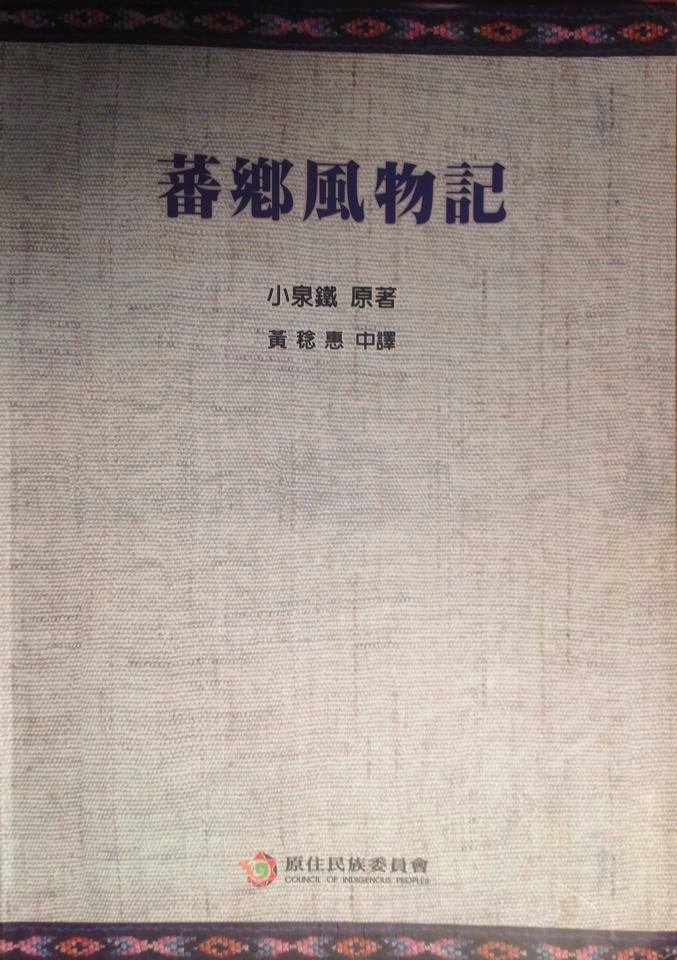廖亦武:病毒時代的讀書筆記
1追憶
作者:宇文所安
《追憶》是一本美到極致的奇書。它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,超過史景遷的絕大部分著作,比如膾炙人口的《王氏之死》。
《追憶》作者宇文所安,耶魯教授,本來的理想是做詩人,只因為詩人要挨餓,所以發奮讀書,做了教授之後,再回過頭來寫詩一樣的學術論文。
許多人把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傳統混為一談,所以全盤否定。甚至把幾千年獨裁的帳,統統算在文化頭上,他們首先要打倒的,就是孔夫子——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——等級制度就是這個該死的孔夫子所倡導。人們卻忘記了,孔夫子也是一個經常破口大罵「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夫,子不子」的流亡者,跟他同時代的所有統治者都談不攏,所以他才自我解嘲: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。」
任何文化的功能,都是人類為了能夠在政治壓迫之下,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及做人的尊嚴;而政治(無論好的還是壞的)終將過去,暴政終將過去——是文化傳統讓歷代知識分子明白這一點,繼而記錄歷史,創造小說、散文和詩歌——個體的生命會消失,而文化的傳承不會中斷,100多年前,卡夫卡寫了《城堡》和《審判》,他非常絕望,甚至覺得後來的讀者,不可能讀懂奧匈帝國的荒誕和窒息。但是,今天,卡夫卡就是經典的代名詞。是一脈相承的文化\文學傳統,讓他得以永生。
回到這本《追憶》,它的開篇,從一首杜甫的詩開始:
岐王宅裡尋常見,
崔九堂前幾度聞。
正是江南好風景,
落花時節又逢君。
這首詩是寫給李龜年的。李龜年是唐高宗時代最有名的樂工,歌喉曾風靡整個長安城,經常與李白等人唱和。杜甫作為晚輩,早年經常在「岐王宅」、「崔九堂」等達官貴人的府上,目睹李龜年的風采——但是後來,安史之亂爆發了,唐高宗出逃,途中遭遇兵變,楊貴妃被弔死在馬嵬坡——世道翻轉,盛唐沒落,長安第一歌星被亂世所挾持,逃到江南,為了糊口,只能在底層茶樓酒肆賣唱——《追憶》就這樣開始了,耶魯教授宇文所安寫道:「老年的李龜年唱中有淚,卻沒認出自己早年的崇拜者杜甫也在觀眾席垂淚。」
我被深深傾倒。這種穿越滄海桑田的審美,在任何時代,都歷久彌新。而共產黨,是這種一吟三嘆的審美的敵人。我曾說過,與其讓共產黨來統治,不如讓一頭豬來統治。因為豬是容易滿足的,而共產黨的胃口,永遠無法滿足。
他們不允許我們有自由審美的樂趣。
2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
作者:劉曉波
劉曉波最後一次入獄前,我沒有讀過這本《末日倖存者的獨白》,因為劉曉波一再對我說「別讀」。後來出逃德國,還是找來讀了。大為震驚。
關於1989的學潮和屠殺,各種親歷者讀物,可謂汗牛充棟。劉曉波自己也寫過其它的、無數的「回顧反思」作品,可恕我直言,除了丁子霖等六四難屬的死難者名單和證詞,只有這一本,讓我難以忘懷。
關於周舵、王丹、馬少方、吾爾開希,等等,等等,這些我多次接觸過的風雲人物,這本書都有寥寥數語、卻入木三分的刻畫,不能不嘆服作者的直覺。
還有一把解剖刀是對準自己的,陰暗、野心和算計也在書中暴露無遺,親愛的曉波,你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,首先就從你人性的袒露、自戕開始——在大屠殺之前,這一切是沒有的——我們曾經激烈爭吵,只因為對某某人、某件事的不同看法,我也曾不辭而別回四川,你的信接二連三追過來,我當時窮途潦倒、憤世嫉俗,政治很不正確;可你也虎落平陽啊,雖然認識不少名演員、名作家、教授、智囊、改革派官員,可人家跟你也不是一路啊……
這本書末尾寫到作者謝絕了友人的邀請,沒有進澳大利亞大使館避難。兩個小時之後,他騎著自行車,突然被警察拿下:「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後悔,痛心疾首地後悔,我為什麽沒有進使館?」
是的,方勵之進了美國使館,許多人也通過黃雀行動逃到香港,劉曉波為什麽沒進使館?
這是一個超越于個人認知的冥冥中的擇決,一個命定的懸念,它一直貫穿了劉曉波之後的人生——四次坐牢,獲得了諾獎,被謀殺在監獄。
2017年7月13日凌晨,我在柏林家中占《周易》銅錢卦,得「明夷」,彖辭翻譯成白話,就是「光明受傷,太陽沉入地心」,囚徒得此一卦,必死無疑;變爻是「既濟」,意思是「他完成了使命」。
3 我喜歡這樣想你
作者:胡慧玲
1989年是繼二戰後,人類歷史最重大的分水嶺,比1966、1968更為關鍵。我們被徹底改變——政治、文化及方方面面。我等也稱之為「八九一代的作家」,斯維拉娜.阿列克塞維奇《二手時間》當然是代表性作品,悲觀的描述和預言,我的書也算吧。胡慧玲的這本也算:要了解台灣的歷史為何如此糾結,這本書是一把鑰匙。
眾所周知,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和柏林牆倒塌.可另外兩次重大事件卻被逐漸淡忘,一是同年3月3日的”拉薩大屠殺”,我曾依據流亡藏人提供的史料,在一篇長文中寫道:「因為西方新聞媒體的缺席,喪心病狂的鏡頭沒被記錄下來。聖城拉薩比皇城北京小十幾倍,八角街廣場也比天安門廣場小十幾倍,可是在如此狹隘的空間,竟有一萬多和平示威者和一萬五千多武裝到牙齒的士兵衝突,其結果,三百多平民死於非命,三千多平民被投入監獄,「罪大惡極者」隨後被判處死刑。位於布達拉宮右側的大昭寺,因為率先升起象徵西藏獨立的「雪山獅子旗」,而被士兵攻佔,寺內至高無上的塔經——它象徵著藏傳密教眾神在世間的尊嚴——被入侵者縱火焚毀。成千上萬的佛教徒為此放聲悲號,不斷有喇嘛撲過去救火,卻不斷被射殺在烈燄之中……」
而另一重大事件發生在1989年4月7日上午9點,<台灣自由時代周刊>總編鄭南榕在警方上門拘捕之際,引爆自焚。《我喜歡這樣想你》中的第一個故事,就是鄭南榕的副手胡慧玲的記錄和追憶,非常具有現場和歷史的痛感。
書中談到,鄭南榕生於1947年228事件當日,父親在日本殖民時期從福建移民過來,娶了本土的媽媽。這樣一個家庭也得應對本土人對外省人的集體仇恨。這種細微的解剖麻雀的筆觸,令人聯想很多,放大開來,就是許多類似族群的、被強加的命運。
本人拜讀過許多遍的,是書中《鄭自才的故事》,關於1970年4月24日的"刺蔣案",江湖傳聞甚多.流亡搖滾歌手段信軍專輯的《寂寞歐羅巴》第一首,就是"黃晴美",她是刺客鄭自才的妻子,也是另一刺客黃文雄的妹妹——胡慧玲的文筆生動曲折,從兩位刺客"到底由誰來開槍"的選擇,到鄭自才的子彈射向蔣經國的剎那,再到被捕入獄,在紐約摩天大樓中的大墓監獄,再到保釋、開庭、逃亡。從美國輾轉到瑞典,立足未穩,又遭引渡,過程之跌宕起伏,堪比當今世界的、同樣被美國通緝的斯諾敦……
不僅如此,本書講述了12個故事,無不應證了魯迅的名言——長歌當哭,須在痛定之後。"對於這個時代的作家,歷史的比較是最為重要的功課。從外部看上去,各種線索的交織特別有意義:作為台灣,先有記憶文化的留存和加固,才有不斷推進的「轉型正義」,德國就是這麽做的。這本書作為時代證詞,值得知識分子重溫。
4 番鄉風物記
作者:小泉鐵
2015年3月,我應邀去台灣參加獨立中文筆會舉辦的文學節,花蓮友人潘小雪贈予了這本《番鄉風物記》,上世紀20年代日本人類學家小泉鐵所著,出版於1932年(昭和七年),是了解台灣人文地理絕佳讀物。
作者親自考察的對象是阿美族和泰雅族,體察入微,毫無偏見,且文筆優雅,與自然、山川、原始部落十分匹配。一般的印象中,原始是蒙昧、封閉、暴力的代名詞,但在這個溫情脈脈的日本人的描寫中,原始就是逝去的、不可追回的一切,唯有文字記錄,讓今天的我們反覆咀嚼。
在《番界日記之二》中,寫到Gaya的贖罪習俗。如果男女發生通姦,被揭露后,女方的兄弟就必須到男方家中,殺一頭豬,豬肉供所有族人分享;如果通姦有了孩子,通姦男女就得長久離開番社,直到孩子長大才能回來——總之,解決問題的方式,幾乎是平和而寧靜的——這是否也有些「寧靜革命」的內涵?
轉型正義比原始正義難度大多了,但是,台灣原住民最初的生存方式(包括解決爭端的方式),還是意味深長的。況且還有那麽多意味深長的部落合唱!
5 百年風雨
作者:李劼
在1980年代的中國文壇,北京劉曉波和上海李劼名聲相當,李劼自己在文章裡說「北劉南李」,的確了得。兩人都擅長做翻案文章,古今中外,但凡正統歷史有定論或公論的人物,都要推倒重來。
天安門大屠殺也改變了兩人的命運,89之後,劉曉波的名字成為禁忌,而李劼雖然不是禁忌,也被他任教的華東師大除名,淪落江湖。我和李劼再次重逢,是在1995年的北京,一塊廝混數日,當時他在寫電視連續劇《吳王金戈越王劍》。
由於舊誼猶存,當我在四川創辦地下人文雜誌《知識分子》,就分別向兩人約稿。劉曉波寄來一篇對前文化部長王蒙的訪談,不久,老兄竟然第三次入獄!多年之後,他遠行了,華文圈出版了他20餘本書,居然都沒有這篇對王蒙的訪談。
而李劼寄來《希特勒和他的行為藝術》。如果倒回去數年,照兩人的名望,如此份量的文稿,海內外名刊將爭相重金訂購,可時過境遷,虎落平陽,只得免費在我這兒違法刊印。
曉波不用說了。這兒單說李劼。毫無疑問,他是文史評論的天才,雖然他的歷史觀我不認同,眾多翻案文章也經不起推敲,可還是被他的生花妙筆所吸引。比如他寫格瓦拉打叢林戰,大意是「格瓦拉一邊開槍一邊咳血,如林黛玉一邊焚詩一邊葬花」,令人絕倒。在他寫的1980年代文學史中,我也佔了一定篇幅,佳評為主,醜化的地方也不少,比如泡妞手法幼稚,還是加拿大人戴邁河像我的書僮,等等,雖胡說八道,可也還有趣。我們又不是共產黨,文人出醜,家常便飯,也有一定審美價值。
前一晌李劼拉黑了我,只因為余英時先生評錢鍾書,稍微有些體諒之意。於是李劼開了火,主打錢先生,附帶也數落余先生墨守儒家成規,沒有「破繭」。我忍不住逗他一句:「余先生快九十了,還說老人家沒『破繭』,摸摸你自己的屁股是不是還拖著蠶絲……」這一來,把這「外表一糾糾肥佬,內裡卻一嬌嬌林妹妹」的這廝惹惱了。
安卓翻牆APP、Windows翻牆:ChromeGo
AD:搬瓦工官方翻牆服務Just My Socks,不怕被牆
儘管如此,他的這本《百年風雨》的確寫得痛快,不管我認為正確與否,都是才華橫溢的一家之言,讀得人如食鴉片,欲罷不能。難怪允晨老闆廖志峰像對林妹妹一樣疼他,他和林榮基,一個出,一個賣,在當今的文化史上,是一段佳話。